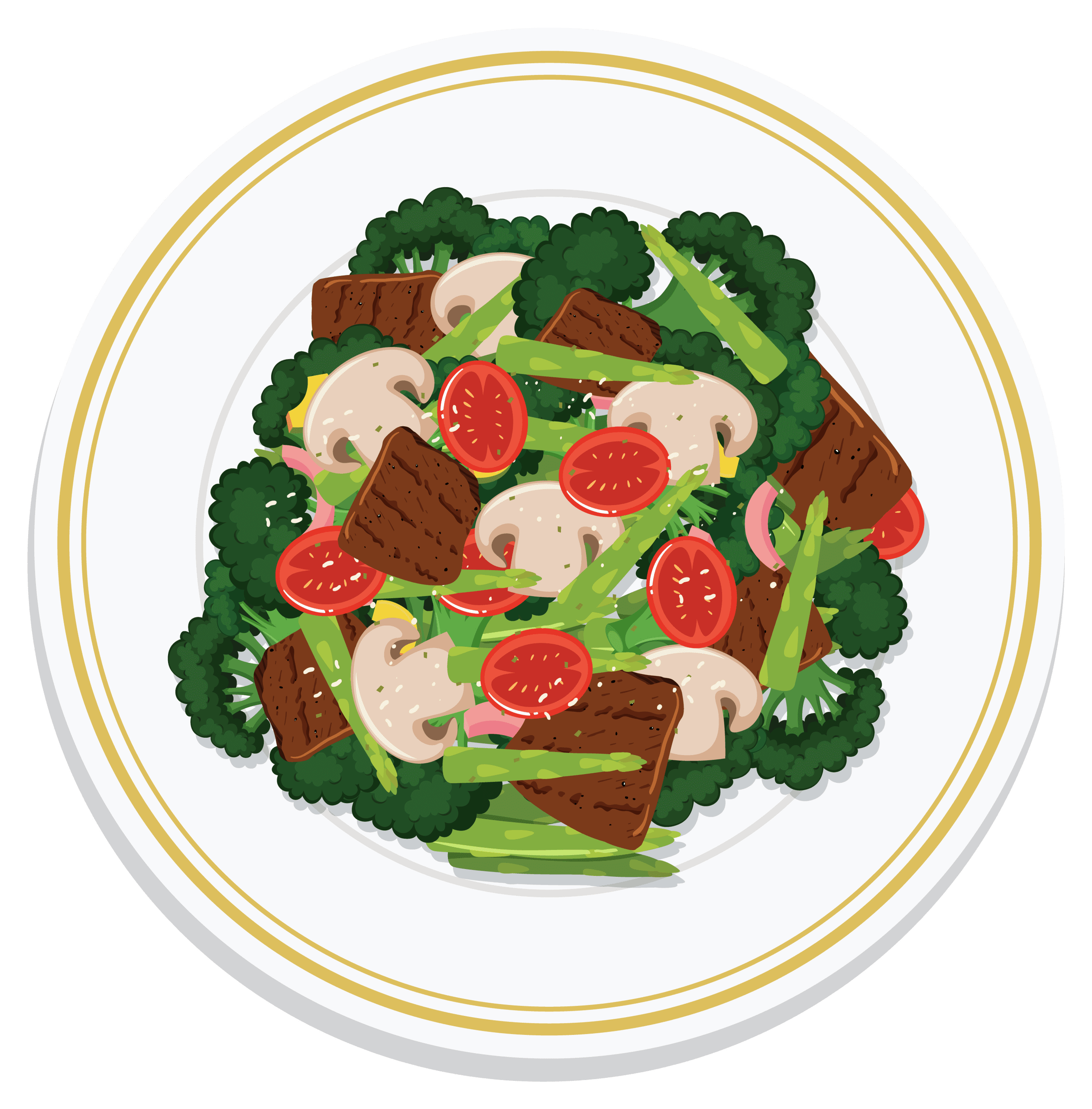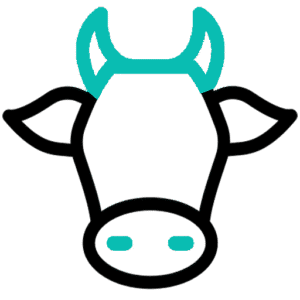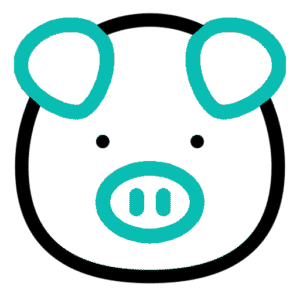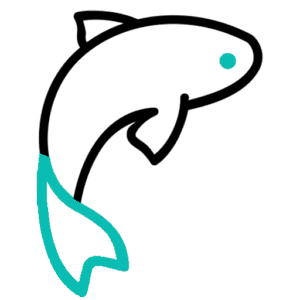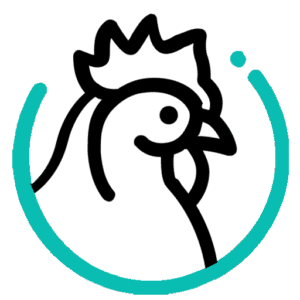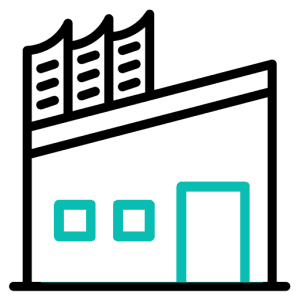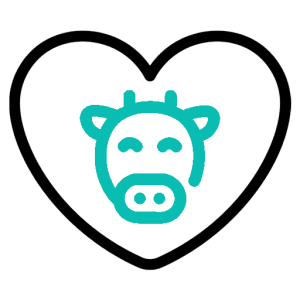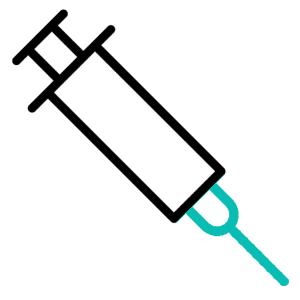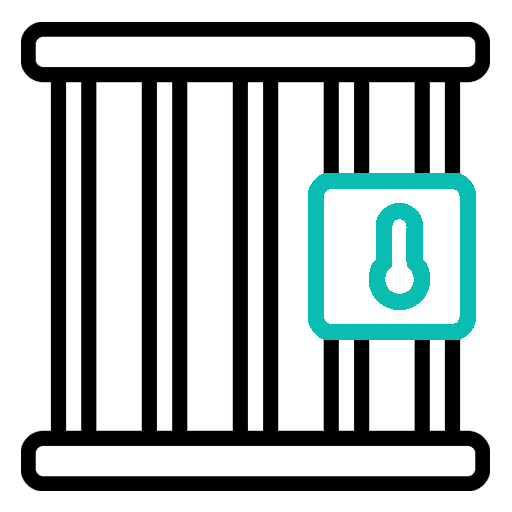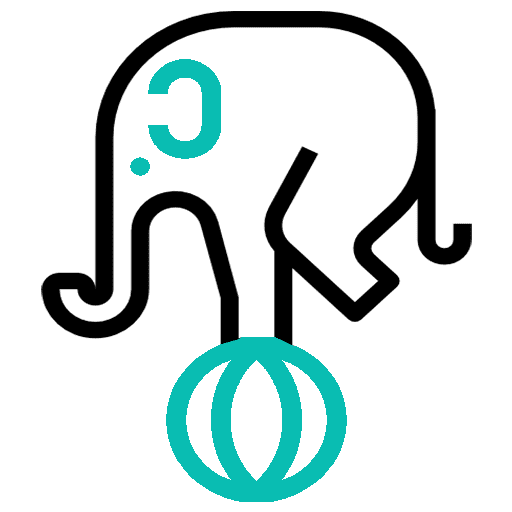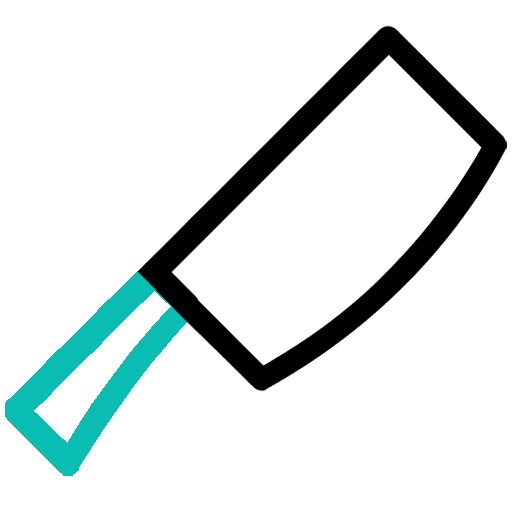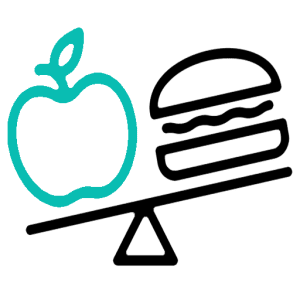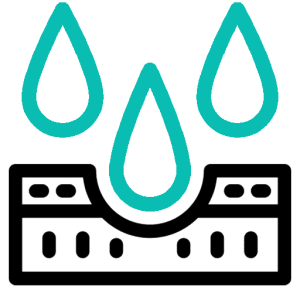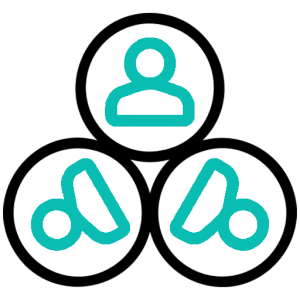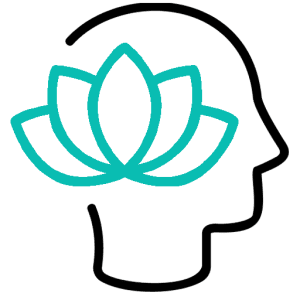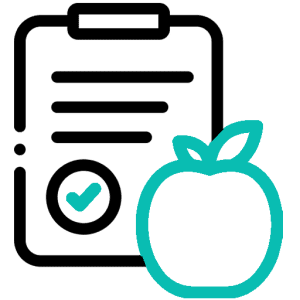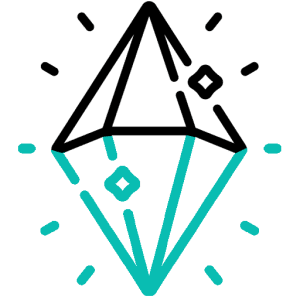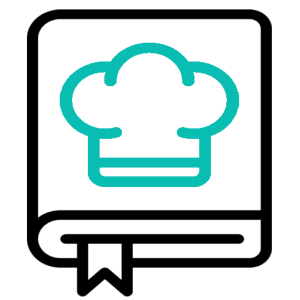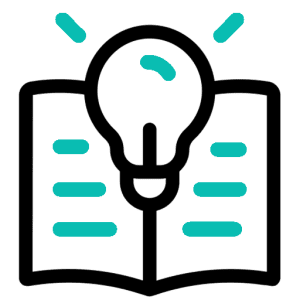墮胎權和動物權的交叉呈現出複雜的倫理景觀,挑戰我們對道德價值和自主權的理解。 爭論經常將眾生的權利與女性對自己身體做出決定的權利進行對立。 本文深入探討了圍繞這些有爭議問題的微妙爭論,探討倡導動物權利是否需要反對墮胎權。
作者首先申明對動物權利的堅定承諾,認為有感知力的動物具有內在的道德價值,這迫使人類停止將它們僅用作資源。 這種觀點不僅限於防止動物遭受痛苦,還包括認識到「它們對繼續生存有著重大的興趣」 作者的立場很明確:殺死、食用或利用有感知力的非人類動物在道德上是錯誤的,法律措施應該反映這種道德立場。
然而,當討論女性選擇墮胎的權利時,討論發生了關鍵轉變。 儘管存在“明顯的衝突”,作者堅定支持女性的“選擇權”,並譴責最高法院可能推翻“羅伊訴韋德案”。 文章講述了作者為正義桑德拉·戴·奧康納(Sandra Day O'Connor) 擔任書記員的經歷,並透過羅伊訴韋德案(Roe v. Wade) 和計劃生育協會訴凱西案(Planned Parenthood v. Casey) 等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案件,強調了墮胎監管的演變。 奧康納提出的「不當負擔」標準被強調是一種平衡的方法,尊重女性的自主權,同時允許國家監管。
作者提出細緻入微的論點,支持動物權 關鍵的差異在於所涉及生物的感知及其所處的情境。 大多數墮胎發生在懷孕初期,當時胎兒還沒有感知能力,而我們所利用的動物無疑是有感知能力的。 此外,作者認為,即使胎兒有感知能力,胎兒與女性身體自主權之間的道德衝突也必須以有利於女性的方式解決。 允許父權法律制度控制「女性」的身體以保護胎兒的生命從根本上來說是有問題的,並且會延續性別不平等。
文章最後區分了墮胎和虐待兒童,強調出生的孩子是一個獨立的實體,國家可以在不侵犯婦女身體自主權的情況下保護其利益。 透過這種全面的分析,作者旨在調和對動物權利的倡導與對婦女選擇權的捍衛,並聲稱這些立場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植根於一致的道德框架。

我倡導動物的權利。 我認為,如果動物具有道德價值而不僅僅是物質,我們就有義務停止將動物用作資源。 這不僅是不讓動物受苦的問題。 儘管有感知力(主觀意識)的動物確實具有不受苦的道德重大利益,但它們也具有繼續生存的道德重大利益。 我相信並提供了論證,認為殺死、食用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有感知力的非人類動物在道德上是錯誤的。 如果在道德問題上有足夠的支持來廢除動物剝削,我當然會支持在法律上禁止它。
那我一定是反對讓女人有選擇要不要孩子的權利嗎? 我必須贊成禁止墮胎的法律,或至少不將墮胎決定視為受美國憲法保護,就像最高法院在 1973 年羅伊訴韋德案那樣,對嗎?
沒有。 一點也不。 我支持婦女的選擇權,我認為由厭女主義者薩姆·阿利托領導並代表包括法官在內的極右翼多數派的法院不誠實地告訴美國人民墮胎是他們會尊重的既定法律,這是非常錯誤的,顯然正計劃推翻 羅伊訴韋德案。
事實上,我在 1982 年 10 月任期期間曾為美國最高法院法官桑德拉·戴·奧康納 (Sandra Day O'Connor) 擔任書記官。生殖健康中心一羅伊訴韋德案中闡明的國家對墮胎的監管,但仍然認可選擇權。 她提出了“不當負擔”標準:“如果特定法規沒有對基本權利造成‘不當負擔’,那麼我們對該法規的評估僅限於我們確定該法規與合法的國家目的合理相關。” 計劃生育訴凱西案中成為國家法律,並允許相對保守的法院達成普遍共識,即選擇權受到憲法保護,受國家監管,但不對選擇權施加「不應有的負擔」。
我在支持婦女的選擇權方面是否前後矛盾,但在主張我們不應該殺死和食用(或以其他方式專門用作資源)有感知能力的非人類動物時,我是否不一致?
沒有。 不是全部。 1995年,我為杜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女權主義與動物選集一篇文章 在那篇文章中,我提出了兩點:
首先,絕大多數墮胎發生在懷孕初期,當時胎兒甚至可以說還沒有知覺。 根據比我 1995 年文章更新的數據 只有大約 1.2% 在 21 週或之後完成。 許多科學家和美國婦科醫師學會認為,27 週是感知能力的下限。 儘管胎兒感知能力的問題仍在爭論中,但共識是,大多數(如果不是基本上所有)流產的人類胎兒都沒有主觀意識。 他們沒有利益產生不利影響。
除了一些軟體動物(例如蛤和牡蠣)之外,幾乎所有我們經常利用的動物無疑都感知能力。 對於非人類的知覺,甚至沒有像對胎兒知覺那樣的懷疑。
但我對選擇權的支持並不是僅僅基於、甚至主要基於胎兒的知覺問題。 我的主要論點是,人類胎兒與我們所利用的非人類動物的情況並不相似。 人類胎兒居住在女性體內。 因此,即使胎兒是有知覺的,即使我們認為胎兒的繼續生存具有道德上的重大利益,胎兒和胎兒所在體內的女性之間也存在著衝突。 解決衝突的方法只有兩種:讓體內有胎兒的女性來決定,或是讓明顯重男輕女的法律制度來做決定。 如果我們選擇後者,那麼實際上就允許國家進入並控制婦女的身體,以維護其對胎兒生命的興趣。 無論如何,這都是有問題的,但當國家的結構有利於男性利益並且生育一直是男性征服女性的主要手段時,問題就尤其嚴重。 看看最高法院。 您認為可以相信他們會以公平的方式解決衝突嗎?
墮胎的婦女與虐待已出生的孩子的婦女(或男子)不同。 一旦孩子出生,孩子就是一個獨立的實體,國家可以保護孩子的利益,但實際上不會控制婦女的身體。
我們利用的非人類動物並不是那些試圖利用它們的人身體的一部分; 它們是獨立的實體,類似於已經出生的孩子。 人類與非人類之間的衝突不需要墮胎方面所需的控制和操縱。 人類和他們試圖利用的非人類是不同的實體。 如果有足夠的公眾支持來停止使用動物(現在肯定沒有),那麼無需國家有效進入和控制任何試圖傷害動物的人的身體,並且在歷史上這種控制發生的背景下,就可以做到這一點一種征服手段。 情況恰恰相反; 作為我們征服非人類的一部分,剝削動物受到鼓勵。 情況並不相似。
我支持選擇,因為我不相信國家,特別是父權國家,實際上有權進入和控制婦女的身體並告訴她必須生孩子。 我確實相信國家有權告訴父母她不能虐待她三歲的孩子,或者她不能殺死並吃一頭牛。 鑑於大多數選擇不生育的女性絕大多數都是在胎兒有感知能力的可能性較低的時候終止妊娠,我認為大多數終止妊娠的決定甚至不涉及有感知能力的利益。
注意:此內容最初發表在abolitionistapphacpercom.com上,不一定反映了 Humane Foundation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