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動物行為研究領域,一種突破性的觀點正在受到關注:非人類動物也可以成為道德主體。
著名動物行為學家喬迪·卡薩米賈納 (Jordi Casamitjana) 深入研究了這一有爭議的想法,挑戰了人們長期以來認為道德是人類獨有特徵的信念。 透過細緻的觀察和科學探究,卡薩米賈納和其他具有前瞻性思維的科學家認為,許多動物具有辨別是非的能力,從而有資格成為道德主體。 本文探討了支持這一主張的證據,研究了不同物種的行為和社會互動,顯示對道德的複雜理解。 從犬科動物的頑皮公平到靈長類動物的利他行為和大象的同理心,動物王國揭示了一系列道德行為,迫使我們重新考慮我們的人類中心主義觀點。 當我們揭開這些發現時,我們被邀請反思我們如何與地球上的非人類居民互動和感知它們的倫理意義。 **簡介:「動物也可以成為道德主體」**
在動物行為研究領域,一種突破性的觀點正在受到關注:非人類動物也可以成為道德主體的概念。 著名動物行為學家喬迪·卡薩米賈納 (Jordi Casamitjana) 深入研究了這一有爭議的想法,挑戰了長期以來認為道德是人類特有特徵的信念。 透過細緻的觀察和科學探究,卡薩米賈納和其他具有前瞻性思維的科學家認為,許多動物具有辨別是非的能力,從而有資格成為道德主體。 本文探討了支持這一主張的證據,研究了不同物種的行為和社會互動,顯示對道德的複雜理解。 從犬科動物中觀察到的頑皮公平,到靈長類動物中的利他行為,再到大像中的同理心,動物王國揭示了一系列道德行為,迫使我們重新考慮我們的人類中心主義觀點。 當我們揭開這些發現時,我們被邀請反思我們如何與地球上的非人類居民互動和感知的倫理意涵。
動物行為學家喬迪·卡薩米賈納 (Jordi Casamitjana) 探討如何將非人類動物描述為道德主體,因為許多動物都有能力區分正確與錯誤
這種事每次都發生過。
當有人強調他們已經發現了人類獨有的特徵時,其他人遲早會在其他動物身上找到這種特徵的證據,儘管形式或程度可能不同。 至上主義者經常利用一些正面的性格特徵、一些智力或一些他們認為是我們物種獨有的行為特徵來證明他們認為人類是「優越」物種的錯誤觀點。 然而,只要有足夠的時間,很可能就會出現證據表明這些並非我們所獨有,而且也可以在其他一些動物中找到。
我並不是說每個人所擁有的特定的獨特基因配置或技能,因為沒有人是完全相同的(甚至雙胞胎也不是),他們的生活也不會是完全相同的。 雖然個體的獨特性也與所有其他物種共享,但這些並不能定義整個物種,而是正常變異性的表現。 我說的是那些被認為是我們物種的「定義」的獨特特徵,它們是典型的,在我們所有人中普遍存在,並且在其他動物中顯然不存在,這些特徵可以更抽像地概念化,以免使它們成為文化,種群或群體。
例如口語溝通的能力、種植食物的能力、使用工具操縱世界的能力等等,所有這些特徵都曾經被用來將「人性」置於一個單獨的「高級」類別之上其他生物,但後來在其他動物身上發現,所以它們對人類至上主義者不再有用。 我們知道,許多動物透過聲音相互交流,語言有時因種群而異,形成“方言”,類似於人類語言的情況(例如其他靈長類動物和許多鳴禽的情況)。 我們也知道,有些螞蟻、白蟻和甲蟲培育真菌的方式與人類培育農作物的方式非常相似。 自從簡·古道爾博士發現黑猩猩如何使用改良的棍子來獲取昆蟲以來,許多其他物種(猩猩、烏鴉、海豚、園丁鳥、大象、水獺、章魚等)也發現了工具的使用
大多數人仍然認為,其中一種「超能力」是人類獨有的:成為道德主體的能力,能夠理解是非,因此能夠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好吧,就像所有其他人一樣,考慮到我們獨特的這一特徵,結果又是另一個傲慢的不成熟的假設。 儘管仍未被主流科學所接受,但現在有越來越多的科學家(包括我)相信非人類動物也可以成為道德主體,因為我們已經找到了足夠的證據表明這一點。
倫理道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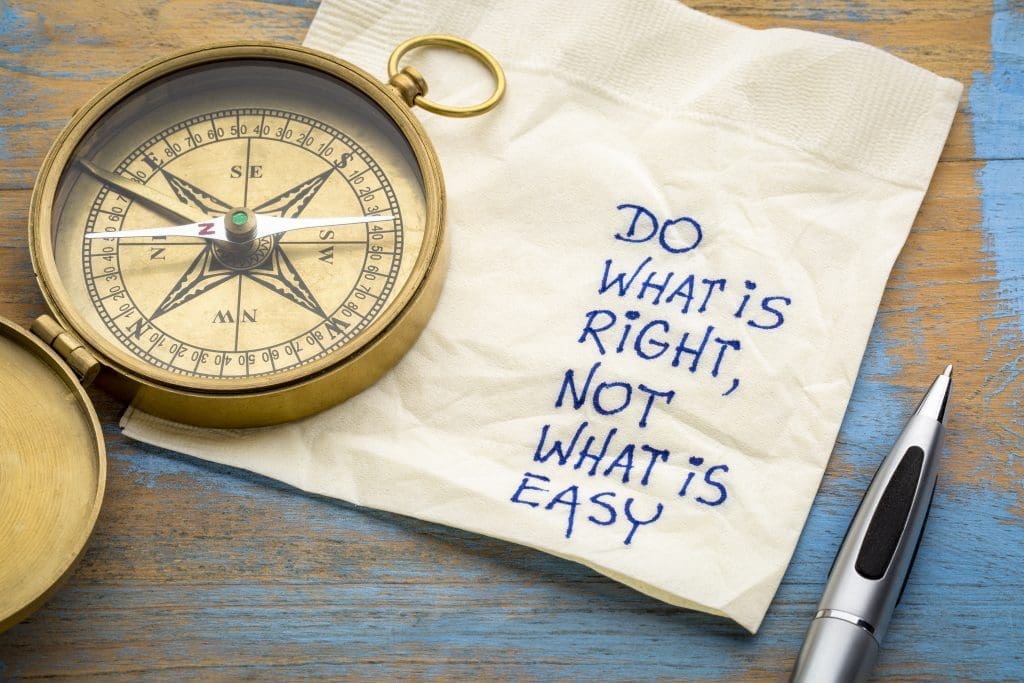
倫理和道德這兩個詞經常被用作同義詞,但它們並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 它們的不同之處對於本文至關重要,因為我聲稱非人類動物也可以是道德主體,但不一定是道德主體。 因此,最好先花一些時間定義這些概念。
這兩個概念都涉及「對」和「錯」的觀念(以及最相對等價的「公平」和「不公平」),以及基於這些觀念來管理個人行為的規則,但區別在於誰的規則我們正在談論。 由外部來源或社會制度認可的特定群體的行為規則,而道德是指基於個人或群體本身是非準則而有關正確或錯誤行為的原則或規則。 換句話說,每個群體(甚至個人)都可以製定自己的道德規則,群體中遵循這些規則的人的行為是“正確的”,而違反這些規則的人的行為是“錯誤的”。 另一方面,那些透過外部製定的規則來管理自己行為的個人或群體,這些規則聲稱更加普遍,不依賴特定群體或個人,他們遵循道德規則。 著眼於這兩個概念的極端,一方面,我們可以找到一種僅適用於一個人的道德準則(該個人制定了個人行為規則並遵循這些規則,而不必與其他任何人分享),而在另一個極端,哲學家可能試圖根據來自所有宗教、意識形態和文化的普遍原則起草道德準則,聲稱該準則適用於所有人類(道德準則可能是哲學家發現的,而不是創造的,因為有些準則可能是自然的、真實的)普遍的)。
作為道德的假設例子,一群共享住宿的日本學生可能會制定自己的生活規則(例如誰打掃什麼,什麼時候應該停止播放音樂,誰支付賬單和房租等)。 。 學生應該遵守規則(做對的事),如果他們違反規則(做錯的事),就會給他們帶來負面後果。
相反,作為道德的假設例子,同一群日本學生可能都是信奉天主教的基督徒,所以當他們做一些違背天主教教義的事情時,他們就違反了他們的宗教道德。 天主教會聲稱其是非規則是普遍適用的,適用於所有人,無論他們是否是天主教徒,這就是為什麼他們的教義基於倫理,而不是道德。 然而,學生的道德準則(他們同意的公寓規則)很可能很大程度上基於天主教會的道德準則,因此違反特定規則可能既違反道德準則,又違反道德準則。術語經常被用作同義詞的原因)。
更令人困惑的是,「倫理學」一詞本身經常被用來標記研究人類推理和行為的公平性和正確性的哲學分支,因此研究與道德和倫理準則相關的問題。 哲學家傾向於遵循三種不同的倫理學派之一。 一方面,「義務論倫理」從行為以及行為者試圖履行的規則或義務來確定正確性,從而確定行為本質上是好還是壞。 倡導這種方法的最有影響力的動物權利哲學家之一是美國人湯姆·雷根,他認為動物具有作為「生命主體」的價值,因為它們有信仰、慾望、記憶和採取行動追求目標的能力。 然後我們有“功利主義倫理學”,它相信正確的行動方針是最大化積極效果的行動方針。 如果數字不再支持功利主義者,他可能會突然改變行為。 他們也可以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而「犧牲」少數人。 最有影響力的動物權利功利主義者是澳洲的彼得·辛格(Peter Singer),他認為「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原則應該適用於其他動物,因為人類和「動物」之間的界限是任意的。 最後,第三個學派是「基於美德的倫理學」學派,它藉鑒了亞里斯多德的著作,亞里斯多德指出,美德(例如正義、慈善和慷慨)使擁有這些美德的人和該人的社會都傾向於他們的行為方式。
因此,人們的行為可能受到他們自己的私人道德、他們所居住的社區的道德、三種道德流派之一(或其中幾種在不同情況下適用)以及宗教或意識形態的特定道德準則的支配。 關於某些特定行為的特定規則在所有這些道德和倫理準則中可能是相同的,但有些可能會相互衝突(並且個人可能有關於如何處理此類衝突的道德規則。
作為一個例子,讓我們看看我目前的哲學和行為選擇。 我將義務論道德應用於消極行為(有些有害的事情我永遠不會做,因為我認為它們本質上是錯誤的),但將功利主義道德應用於積極行為(我嘗試首先幫助那些需要更多幫助的人,並選擇最有利於個人的行為) 。 我不信教,但我是一個有道德的素食主義者,所以我遵循素食主義哲學的倫理(我認為素食主義的主要公理是所有正派人類都應該遵循的普遍原則)。 我自己住,所以我不必遵守任何「公寓」規則,但我住在倫敦,我遵守倫敦好人的道德,遵循公民成文和不成文的規則(例如站在右邊)在自動扶梯上)。 身為動物學家,我也遵守科學界道德的專業行為準則。 我使用純素協會對純素主義的官方定義作為我的道德底線,但我的道德促使我超越它,並在比嚴格定義更廣泛的意義上應用它(例如,除了盡量不傷害有情眾生)素食主義要求,我也盡量避免傷害任何生物,無論是否有知覺)。 這讓我盡量避免不必要地殺死任何植物(即使我並不總是成功)。 我還有一條個人道德規則,如果我有可行的公共交通選擇,我會盡量避免在春季和夏季使用公共汽車,因為我想避免乘坐不小心殺死飛蟲的車輛。 因此,我的行為受到一系列倫理和道德準則的約束,其中一些規則與他人共享,而另一些則不然,但如果我違反其中任何一條,我認為我做錯了(無論我是否有被「抓住」或我因此受到懲罰)。
非人類動物的道德機構

馬克·貝科夫(Marc Bekoff)是主張承認某些非人類動物有道德的科學家之一最近有幸採訪了他。 他研究了犬科動物(如土狼、狼、狐狸和狗)的社交遊戲行為,透過觀察動物在遊戲過程中如何相互作用,他得出結論,它們有道德準則,有時會遵守,有時會違反,當阻止它們會產生負面後果,讓個人了解群體的社會道德。 換句話說,在每個玩耍的動物社會中,個體都會學習規則,並透過公平感來了解什麼行為是正確的,什麼行為是錯誤的。 在他頗具影響力的著作《動物的情感生活》(新版剛出版)中,他寫道:
「就其最基本的形式而言,道德可以被認為是一種『親社會』行為——旨在促進(或至少不減少)他人福祉的行為。 道德本質上是一種社會現象:它產生於個體之間的互動中,它作為一種織帶或織物而存在,將複雜的社會關係編織在一起。 道德這個詞從此成為區分對與錯、好與壞的簡寫。
貝科夫和其他人發現,非人類動物在玩耍時表現出公平性,並且它們對不公平行為做出負面反應。 違反遊戲規則的動物(例如咬得太用力或在與比自己年輕得多的人玩耍時沒有降低身體動作的力度,這被稱為自我設限)會被群體中的其他人視為做錯了事,並且在其他社交互動中要么被訓斥,要么沒有受到優待。 做錯事的動物可以透過請求寬恕來糾正錯誤,這可能會起作用。 在犬科動物中,玩耍時的“道歉”會採取特定姿勢的形式,例如“玩耍弓”,由背線向下傾斜到頭部、尾巴保持水平到垂直但不低於背線、放鬆的身體和臉部,耳朵位於頭骨中部或前方,前肢從爪子到肘部接觸地面,尾巴搖動。 玩耍弓也是表示「我想玩」的身體姿勢,任何在公園裡看狗的人都能認出它。
貝科夫寫道: 「狗不能容忍不合作的作弊者,他們可能會被避開或被趕出遊戲小組。 當狗的公平感受到侵犯時,就會產生後果。 當貝科夫研究郊狼時,他發現,那些因為被其他人避開而不像其他郊狼那樣玩耍的郊狼幼崽更有可能離開群體,而這會增加死亡的機會,這是有代價的。 在懷俄明州大提頓國家公園對郊狼進行的一項研究中,他發現離開群體的一歲狼有 55% 死亡,而留在群體中的狼只有不到 20% 死亡。
因此,透過從玩耍和其他社會互動中學習,動物為自己的每一個行為貼上「對」和「錯」的標籤,並學習群體的道德(這可能是與另一個群體或物種不同的道德) 。
道德主體通常被定義為有能力辨別是非並對自己的行為負責的人。 我通常使用「人」這個詞作為一個具有獨特個性、具有內在和外在身份的存在,所以對我來說,這個定義同樣適用於無知覺的存在。 一旦動物了解了它們所處的社會中哪些行為被認為是正確的、哪些行為是錯誤的,它們就可以根據這些知識選擇如何行事,成為道德主體。 他們可能本能地從基因中獲得了一些此類知識,但如果他們透過玩耍或社交互動來學習,那麼一旦他們成年並知道正確行為和錯誤行為之間的區別,他們就成為對行為負責的道德主體。 他們的行為(只要他們在生物學的正常參數範圍內精神健全,就像人類在審判中經常出現的情況一樣,只有當他們是精神上有能力的成年人時才能被判有罪)。
然而,正如我們稍後將看到的,違反道德準則只會讓您對持有該準則的團體負責,而不是對您未訂閱的具有不同準則的其他團體負責(用人類的術語來說,這是非法的,甚至是不道德的事情)一個國家或文化可能在另一個國家或文化中是允許的)。
有些人可能會認為非人類動物不能成為道德主體,因為它們別無選擇,因為它們的所有行為都是本能的,但這是一種非常老式的觀點。 動物行為學家現在達成共識,至少在哺乳類和鳥類中,大多數行為都來自本能和學習的結合,先天與後天的黑白二分法不再站得住腳。 基因可能會導致某些行為,但發育過程中環境的影響以及一生中的學習可以將它們調節到最終形式(這可能會根據外部環境而變化)。 這也適用於人類,因此,如果我們接受人類及其所有基因和本能都可以成為道德主體,那麼就沒有理由相信在具有非常相似的基因和本能的其他動物(尤其是其他社會動物)中找不到道德主體。 至上主義者希望我們對人類應用不同的行為標準,但事實是,我們的行為庫的發展沒有質的差異來證明這一點是合理的。 如果我們承認人類可以成為道德主體,而不是不對其行為負責的決定性機器,那麼我們就不能否認其他能夠透過經驗學習和調節行為的社會動物也具有同樣的屬性。
非人類動物道德行為的證據

為了找到非人類動物的道德證據,我們只需要找到個體認識並玩耍的社會物種的證據。 有很多這樣做的。 地球上有數以千計的社會性物種,大多數哺乳動物,甚至是那些來自孤獨物種的哺乳動物,在年輕時都會與它們的兄弟姐妹一起玩耍,但是儘管所有這些都將利用遊戲來訓練它們的身體,以達到成年後需要完善的行為,但社會性哺乳動物和鳥類也會透過遊戲來了解他們的社會中的誰是誰,以及他們的群體的道德規則是什麼。 例如,諸如以下規則:不要從等級制度中比你高的人那裡偷食物,不要對嬰兒太粗暴,訓練他人以求和解,不要與不想玩的人一起玩,不要與其他人一起玩。允許亂搞某人的嬰兒、與你的後代分享食物、保護你的朋友等等。的那樣),我們會使用諸如此類的術語誠實、友誼、節制、禮貌、慷慨或尊重——這些都是我們賦予道德人的美德。
一些研究發現,非人類動物有時願意以自己的代價幫助他人(這稱為利他主義),要么是因為它們知道這是群體成員期望它們的正確行為,要么是因為它們的個人道德(後天的或先天的,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引導他們這樣做。 這種類型的利他行為已經在鴿子(Watanabe and Ono 1986)、老鼠(Church 1959;Rice and Gainer 1962;Evans and Braud 1969;Greene 1969;Bartal et al. 2011;Sato et al. 2015)和一些動物身上表現出來。等人,2010 年;Horner 等人,2011 年;Schmelz 等人等2017)。
在鴉科動物(Seed et al. 2007;Fraser and Bugnyar 2010)、靈長類動物(de Waal and van Roosmalen 1979;Kutsukake and Castles 2004;Cordoni et al. 2006;Fraser et al.)中也發現了同理心和關心他人的證據。 2012 年);大象(Plotnik 和de Waal,2014 年);虎皮鸚鵡(Ikkatai 等人) . 2016)、馬(Cozzi et al. 2010)和草原田鼠(Burkett et al. 2016)。
不平等厭惡(IA),即對公平的偏好和對偶然不平等的抵制,也存在於黑猩猩(Brosnan et al. 2005, 2010)、猴子(Brosnan and de Waal 2003;Cronin and Snowdon 2008;Massen et al 2012 年)中。
如果人類看不到其他物種的道德,即使他們擁有的證據與我們在看待不同群體的人類行為時所接受的證據相似,這只能表明人類的偏見,或者是壓制他人道德行為的努力。 蘇珊娜·蒙索 (Susana Monsó)、朱迪思·本茨-施瓦茨堡 (Judith Benz-Schwarzburg) 和安妮卡·布雷姆霍斯特 (Annika Bremhorst) 是 2018 年論文《動物道德:它意味著什麼以及為何重要》的作者,他們整理了上述所有參考文獻,總結道:「我們發現了許多背景,包括動物道德中的常規程序。」農場、實驗室和我們的家中,人類可能會幹擾、阻礙或破壞動物的道德能力。
甚至有人看到一些動物個體自發性地與其他物種的成員(人類除外)玩耍,稱為種內社交遊戲(ISP)。 據報道,靈長類動物、鯨目動物、食肉動物、爬行動物和鳥類中都有這種情況。 這意味著其中一些動物遵循的道德可能會與其他物種交叉——也許更傾向於哺乳動物或脊椎動物的道德規則。 如今,隨著社交媒體的出現,我們可以找到大量視頻,展示不同物種的動物互相玩耍——並且似乎理解它們的遊戲規則——甚至以一種看似完全無私的方式互相幫助——做我們應該描述為有道德的人所特有的善行。
每天都有越來越多的證據反對人類是地球上唯一道德存在的觀念。
對野生動物痛苦辯論的影響

國際暢銷回憶錄《哲學家與狼》認為,有些非人類動物可能是有道德的生物,它們可以根據道德動機行事。 他指出,道德情感包括“同情、慈悲、仁慈、寬容和耐心,以及與之相對應的消極情緒,如憤怒、憤慨、惡意和怨恨”,以及“公平感和不公平感”。非人類動物中找到。 然而,他表示,雖然動物可能缺乏對其行為承擔道德責任所必需的概念和後設認知能力,但這只是將它們排除在道德主體之外。 我同意他的觀點,除了後來的斷言,因為我相信道德存在也是道德主體(正如我之前所說的)。
我懷疑羅蘭茲說,由於野生動物苦難辯論的影響,一些非人類動物可以是道德存在,但不是道德主體。 其核心是關心他人痛苦的人是否應該嘗試透過幹預捕食者/獵物相互作用以及其他非人類動物造成的其他形式的痛苦來減少野生動物的痛苦。 許多素食主義者,像我自己一樣,主張不干涉自然,不僅專注於防止人類擾亂被剝削動物的生活,甚至放棄一些我們偷來的土地並將其歸還給自然(我寫了一篇關於這一點的文章,題為《素食主義者》)重新野化的案例)。
然而,少數素食主義者不同意這一點,並訴諸自然謬論,認為野生動物遭受其他野生動物造成的痛苦也很重要,我們應該幹預以減少這種痛苦(也許可以阻止掠食者殺死獵物,甚至減少野生動物的大小)。 「掠奪消除論者」確實存在。 動物倫理和野生動物倡議等組織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的一些成員(不是全部)一直在倡導這種觀點。
主流素食主義者群體對這種不尋常且極端的觀點最常見的回應之一是,野生動物不是道德主體,因此捕食者不應為殺死獵物承擔責任,因為他們不知道殺死其他有情眾生可能是一種行為。 因此,當這些素食主義者看到像我這樣的人說非人類動物也是道德主體(包括野生掠食者)時,他們會感到緊張,並希望這不是真的,這並不奇怪。
然而,沒有理由緊張。 我們聲稱非人類動物是道德主體,而不是道德主體,考慮到我們之前討論的這兩個概念之間的差異,這使我們仍然能夠同時持有我們不應該幹預的觀點在自然界中,許多野生動物都是道德主體。 關鍵在於,道德主體只有在違反其道德準則之一時才會犯錯,但他們不對人類負責,而只對那些與他們「簽署」道德準則的人負責。 一隻做錯事的狼只對狼族負責,而不對象族、蜜蜂族、人類族群負責。 如果那隻狼殺了人類牧羊人聲稱擁有的羔羊,牧羊人可能會覺得狼做錯了什麼,但狼並沒有做錯什麼,因為他沒有違反狼的道德準則。
正是承認非人類動物可以成為道德主體,更強化了不干涉自然的態度。 如果我們將其他動物物種視為“民族”,那就更容易理解了。 同樣,我們不應該幹預其他人類國家的法律和政策(例如,道德素食主義在英國受到法律保護,但在美國尚未受到保護,但這並不意味著英國應該入侵美國來糾正這一點)問題)我們不應該幹預其他動物國家的道德準則。 我們對自然的干預應僅限於修復我們造成的損害,並從真正能夠自我維持的自然生態系統中“撤出”,因為在這些生態系統中,淨痛苦可能比任何人造棲息地(或自然棲息地)都要少。
放任自然並不意味著忽視我們遇到的野生動物的痛苦,因為這將是物種歧視。 野生動物和家養動物一樣重要。 我贊成拯救我們遇到的受困動物,治癒受傷的野生動物,讓它們重新回到野外,或讓無法獲救的痛苦野生動物擺脫痛苦。 在我的《道德素食主義者》和我提到的文章中,我描述了我用來決定何時進行幹預的「折磨參與方法」。 不干涉自然意味著承認自然的主權和人類的錯誤,並將不干涉生態系統的「反物種主義野化」視為可接受的干預措施。
貓和狗的道德主體可能是另一回事,因為許多伴侶動物都與人類伴侶「簽署」了一份合同,因此它們擁有相同的道德準則。 「訓練」貓和狗的過程可以看作是這種合約的「談判」(只要不厭惡並且同意),並且許多貓和狗對這些條款感到滿意,只要他們同意提供食物和住所。 如果它們違反了任何規則,它們的人類同伴會以各種方式讓它們知道(任何與狗一起生活的人都見過它們在知道自己做錯事時經常向你展示的“內疚的表情”)。 然而,一隻被當作寵物圈養在籠子裡的奇異鳥並沒有簽署這份合同,所以任何試圖逃跑而造成的傷害都不應該導致任何懲罰(那些圈養牠們的人類才是錯誤的人)。
非人類動物作為道德主體?

說非人類動物可以成為道德主體,並不代表所有物種都可以,或所有可以成為道德主體的個體都可以成為「好」動物。 這不是要天使化非人類動物,而是要提升其他動物的水平,並將我們從虛假的基座上移除。 就像人類一樣,個體非人類動物也可以是好人或壞人,聖人或罪人,天使或惡魔,並且與人類一樣,在錯誤的環境中與錯誤的人在一起也可能會腐蝕它們(想想鬥狗) 。
老實說,我更確定人類不是地球上唯一的道德主體,而不是所有人類都是道德主體。 大多數人還沒有坐下來寫下他們的道德規則,也沒有花時間考慮他們想要遵守哪些道德和倫理準則。 他們傾向於遵循其他人告訴他們要遵循的道德規範,無論是他們的父母還是所在地區的主導思想家。 我認為,選擇向善的非人類動物比盲目追隨地理抽籤分配給他們的宗教的人類更有道德。
讓我們以傑思羅為例。 他是馬克·貝科夫的狗夥伴之一。 給伴侶動物餵食植物性食物的素食主義者經常說這些伴侶是素食主義者,但這可能不是真的,因為素食主義不僅僅是一種飲食,而是一種人們必須選擇堅持的哲學。 然而,我認為傑思羅可能是一隻真正的純素狗。 在他的書中,馬克講述了傑思羅在他所居住的科羅拉多州的荒野中遇到其他動物(如野兔或鳥類)時不僅不殺死它們,而且在它們遇到麻煩時拯救它們並將它們帶到馬克身邊的故事。 馬克寫道:「傑思羅熱愛其他動物,他拯救了兩隻動物。 他可以毫不費力地輕鬆吃掉每一個。 但你不會對朋友這樣做。 「我推測馬克餵傑思羅植物性食物(因為他是素食主義者並且了解當前的研究),這意味著傑思羅實際上可能是一隻素食狗,因為除了不食用動物產品,他也擁有自己的飲食習慣。 作為道德主體,他選擇不傷害他人,而作為素食主義者,他選擇基於不傷害他人原則的素食主義哲學(不僅僅是吃素食的人),他可能更與一個只吃植物性食物並一邊自拍的青少年影響者相比,他是素食主義者。
像我這樣的動物權利素食主義者不僅持有素食主義哲學,還持有動物權利哲學(兩者有很大重疊,但我認為它們仍然是分開的)。 因此,我們一直說非人類動物有精神權利,我們爭取將這種權利轉化為法律權利,防止人們剝削它們,讓非人類動物個體被視為不可殺害的法人,受到傷害或被剝奪自由。 但當我們在這種情況下使用「道德權利」一詞時,我們通常指的是人類社會內的道德權利。
我認為我們應該進一步宣稱非人類動物是道德主體,擁有自己的道德權利,干涉這些權利是對我們人類應該遵循的道德原則的侵犯。 我們不應該賦予非人類動物權利,因為它們已經擁有這些權利並靠它們生活。 在人類進化之前他們就已經擁有它們了。 我們有責任改變自己的權利,並確保侵犯他人權利的人受到停止和懲罰。 侵犯他人的基本權利就是違反人類所簽署的道德原則,這應該適用於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所有簽署成為人類一部分的人(以及此類成員所享有的所有特權)。
肉慾至上是一條肉食主義者的,二十多年前我成為素食主義者後,我就不再相信它了。 從那時起,我不再相信那些聲稱自己找到了只有人類才擁有的「美德」的人。 我確信非人類動物是它們自己道德中的道德主體,與我們的道德無關,因為它在我們出現之前就已經建立了。 但我想知道他們是否也可以是有道德的人,是有道德的代理人,並遵循人類哲學家最近才開始識別的普遍正確和錯誤原則。
目前還沒有太多證據證明這一點,但我認為如果我們更關注非人類動物與其他物種的行為方式,這一點很可能會到來。 也許行為學家應該多研究種內社會遊戲,哲學家應該研究人類以外的道德的共通性,看看是否會出現一些東西。 如果確實如此,我不會感到驚訝。
每當我們敞開心扉接受我們的平凡本性時,就會發生這種情況。
注意:此內容最初發表在veganfta.com上,可能不一定反映了 Humane Foundation的觀點。














































